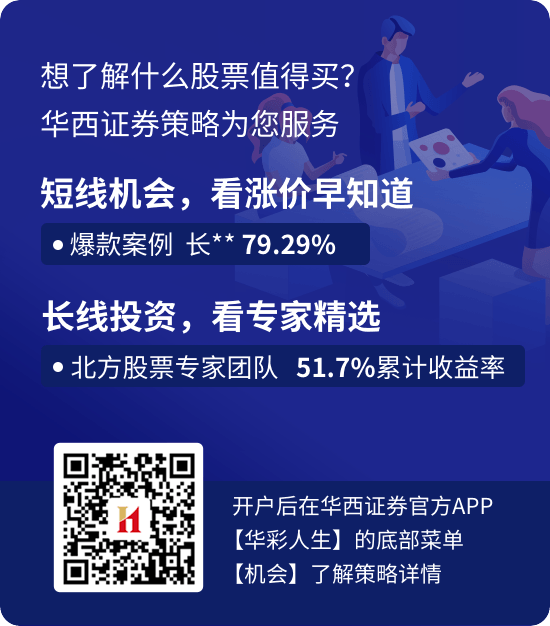81岁的理查德·桑德尔(Richard Sandor)戴着他标志性的牛仔草帽,笑意盈盈地注视着镜头。两排20世纪纪实摄影藏品悬挂在墙上,在镜头的视角中,恰好在身后延伸成两根相交的直线。
这正是这位“碳交易之父”关于地球治理和人类生存的绝妙缩影:二氧化碳的无形资产、市场化机制的无形之手,相汇在这个宏大的未来命题下。
这已经是桑德尔好几次露面在中国碳市场活跃者的视野中了。他用朴实的英文词汇,一字一顿地点评欧盟、美国和中国的碳发展故事。
7月16日,刚满周岁的中国碳市场在体量上已经一跃成为世界第一。
而在这位最早将二氧化碳的排放权作为商品进行交易、以市场化机制约束碳排放行为的开创者眼中,这个庞然大物或许还需要二十年的成长期。
“保持决策制定和执行方面的耐心是最重要的。”他慢悠悠又有力地说。
时间之尺
过去几十年,人类对二氧化碳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地下捕获二氧化碳的想法源于1977年。它不是来自农场,而是从美国的油田开始的。天然气总管的工人将二氧化碳输送到附近的油井中,帮助石油从原本无法到达的矿床中挤出,这套可以提高采油率的工艺沿用至今。
但是,当1992年联合国成员国领导人在里约会议上,根据 1989 年联合国大会决议制定的气候计划讨论应对气候变化引起的海平面上升时,全球解决二氧化碳问题的想法产生了。
差不多这个时候,桑德尔也从加州伯克利大学的一名教授,变成了一位长袖善舞的气候变化企业家。现在他的名片上写着: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的创始人、美国金融交易所AFX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右翼总是怀疑你是一个爱护树木的环保主义者,而左翼则指责你是一个贪财的资本家,”桑德尔对华尔街见闻说,“我认为自己是一名环保主义者,但我将这些情绪与日常工作分开。”
作为一名商业游戏的制定者,桑德尔参与了世界上第一个二氧化硫限额交易市场、美国自愿减排市场、欧盟碳交易市场的建立。他也是中国碳市场的老朋友,在筹建天津碳交易市场时深度参与其中。
这样一位精通中外碳交易的专家口中,现在要给刚满一岁的中国碳交易市场下考语还非常困难。
“我观察到,这个市场和欧盟、美国的市场都不一样,首先是美国,人们往往会忘记美国是一个联邦公共机构,华盛顿的政策就只是在华盛顿生效,各州主要推行的是区域市场,在美国,我们有20个碳市场和可再生能源市场。”桑德尔表示,北美现在的碳市场大致与黄金市场的规模相当。
相比之下,中国集中的大体量确实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势能。
去年7月16日才上线的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从周岁成绩单来看不乏亮眼的数字:截至7月11日收盘,开市以来累计成交碳排放配额1.94亿吨,累计成交额84.90亿元;
第一个履约周期中,纳入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2162家,年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约45亿吨二氧化碳,履约完成率达到了99.5%;
碳价从48元/吨起步,一度涨至61.07元/吨,7月11日碳排放配额挂牌协议收盘价报58元/吨,较起始价格上涨10元/吨……
“市场是有机的,一定需要时间来成长,一年前《华尔街日报》就说中国将推出世界上最大的排放交易计划,现实情况是,市场总是需要20年的时间来成长,从‘童年’成长到‘年轻人’大概需要8年,然后再需要十几年来达到成熟。”桑德尔表现出更加审慎乐观的态度。
过渡设计
“如果仔细看,中国其实是一个碳排放强度控制的市场,而非简单的碳排放总量控制,所以设计机制也与欧洲、美国的市场不同,我们常说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要由中国自己的经济学家来设计的,由中国的市场从业者来满足其需求,”桑德尔告诉华尔街见闻,碳排放强度实际上会随时间推移而变化,有可能会被碳排放总量控制所取代,所以现在还是一个过渡性的制度设计。
事实上,碳强度控制制度确实与中国碳排放交易体系中的“配额分配—配额履约—配额交易”逻辑不尽匹配。
碳排放目标的制定和落实是碳排放总量控制的基础,而中短期碳排放总量目标一直未明确可能限制长期目标的实现。
“现有的碳排放达峰目标只要求排放总量在某个时间达到最高值后逐步下降,而没有明确总量控制的天花板,从国家到各地方的碳达峰目标都没有确定具体的控制数量,从而导致部分地区在正式碳达峰的时点前争取多安排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的‘攀高峰’现象,这可能造成碳排放总量增长的失控和资源的大量浪费。”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资深研究员卞勇解释道。
对明确碳排放总量的谨慎态度主要是来源于对总量目标可能约束经济增长的担忧,所以,碳排放控制目标自“十二五”以来只有“碳强度”这一非刚性的约束,导致了只要经济增速足够快即可实现目标的现象。
“各地更加重视把地区生产总值这一分母做大,而不太关注碳排放总量这一分子的减小。”卞勇如是说。
以碳排放总量作为直接性指标,才能与国家自主贡献文件中提出的2030年峰值目标更加匹配。不过,曾经经历过多个市场成长期的桑德尔多次强调,“不能对一个刚运行一年的市场妄下断论。”
发展规律
“欧盟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是在2005年启动的,其体量在最初也不是很大,在《京都议定书》承诺期的四年前,交易价格降到了0元,2009年启动的RGGI价格也曾跌到将近1美元,2013年启动的加州碳市场也出现过低价格的情况,在几乎每个我们熟知的案例中,我们都能看出,市场运行一年的结果是无法反映其未来的表现的。”桑德尔对华尔街见闻表示。
他以一个从业30年、全球总量控制下的碳交易市场研究者的身份强调,中国的碳交易之行才刚刚起步。
根据多方梳理发现,中国的碳市场建立的确经历了相对较长的一段铺垫时间。最初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之时,中国主要将其看成一个环境问题,并没有意识到背后蕴含的政治与经济影响。
《京都议定书》的签署才让中国模糊地认识到经济发展和贸易在未来可能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但是由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原则的存在,前两期中国相应的减排义务较少,甚至还有一定的减排富余可以转而与高排放量的国家进行交易。
所以中国进入世界碳交易体系最初主要是以清洁能源机制(CDM)中单纯卖家的身份,获得了不少实质性的收益,并没有考虑自身碳市场的构建。
然而,顶层设计者已经开始隐隐意识到国际环境的变化。2011年,国家发改委批准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和深圳七个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
2013年后,由于国际CDM需求和国际政治环境发生额较大变化,特别是《京都议定书》履约期的持续性问题,中国CDM项目开发和签发果然趋于停滞。
2017年12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终于率先从发电行业启动。
2020年12月到2021年3月间,生态环境部连续发布了几个针对全国碳市场(发电行业) 管理的纲领性文件。
2022年7月16日,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上线了。
桑德尔对华尔街见闻表示:“我们需要从一个长远的眼光来进行评判,我们不能只看中国的碳交易现状,还要结合未来两年的发展情况,我强烈建议政策的制定者与行业从业者保持耐心。这一市场需要经过更多几年的发展,我们才能对其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也许在3年后我们才能看到这个市场的全貌。”
Refinitiv路孚特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中国碳市场也面临监测、报告与核查(MRV)方面的运营挑战和困难,主要的挑战包括缺乏透明的基础数据和碳交易专家,受访者认为,MRV相关的技术问题以及第三方核查机构经验不足是中国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亟待解决的问题。
桑德尔的观点也应证了调查结果。“中国碳交易市场面临的重要挑战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是一样的,即最终建立MRV系统。相关机构的建立十分重要,这意味着需要培养相关的大学教授、学生、监管者、律师、会计师、交易者以及那些能实现技术变革的人,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时间”和“耐心”始终是他的核心关键词。
“全球只有一个碳市场的愿景不见得是正确的。我们可能会看到我所谓的多边市场,这也是棉花交易和小麦交易发生的方式。我们并不是一下子就有了一个大的多国协定,而是这些市场在本国不断发展。我认为中国市场的设计其实是不错的。通过向其他市场学习,迈出了很好的第一步。中国想要交易超过40亿吨的碳排放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碳交易市场,只是需要时间。”